| 短評臺灣資本主義發展與原住民社會反體制運動
文/傅君‧圖/林頌恩

「假觀光‧真滅族」的議題,同樣牽扯臺灣在資本主義發展向錢看的過程,帶給原住民族社會在土地權、人權、文化與信仰等方面的失落。 |
發源於14、15世紀地中海地區,而在18、19世紀,隨著歐洲帝國主義席捲全球的資本主義體制,到了20世紀90年代以後,又隨著全球化以及「共產主義」集團的解體(包括蘇聯解體、中國「改革開放」),已成為真正全球性的主導性政治經濟實體。
在「資本家」無止盡地追求利潤的推動力之下,資本家一則以運用勞動者(廣義而言,「勞動者」指不擁有「資本」而為擁有「資本」的企業主生產的人)從事生產、將產品在市場中銷售而創造利潤(所謂「營利所得」);另一個途徑,則是將生產過程的「負面」(有損「利潤」)的面向,加以「外部化」。
在運用勞動者的生產勞動創造利潤方面,資本家為了將「利潤」極大化,通常採取壓低勞動者所得的途徑,或者是從事研發,以透過生產技術革新來降低生產成本,而技術革新也可以與勞動力配置結合,以降低產品的單位成本並提高利潤。

政府常以開發與促進繁榮之名要原住民交出生死依賴的土地另做他用,引發民怨與抗爭。 |
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資本家對勞動者的「運用」,導致各種「反體系運動」(anti-systemic movement)(「世界體系」理論的社會學家Immenual Wallerstein)的用語),表現在婦女解放、性別解放、族群運動等各種「公民運動」之中;在將生產過程的負面效益「外部化」方面,資本家將生產過程的廢棄物,轉嫁到整個社會或其他國家,由他人吸收。
總的來說,英文中有一句俚語” A dollar saved, is the dollar earned”,在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過程中,對於「外部化」的反制運動,則可以環保運動為顯眼的例子。當然,從資本的角度,對勞動力的剝削也可以看作是一種「外部化」的手段──把薪資成本轉嫁到勞動者本身(壓低工資、增加工時以壓低單位成本、降低勞動條件──不改善工作條件、不給福利等等),由勞動者本身來吸收,即一般所謂的「廉價勞工」。
至於「外部化」的例子可說不勝枚舉。隨著經濟與工業水平的發展,1980年代起,臺灣將被50年代起發展的現代化農業生產的累積所扶植起來對環境衝擊高的水泥、石化、以及勞力密集的紡織等日用商品工業,轉移到工資、環保標準低的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大陸等所謂「投資環境」優良的國家及地區都是例子。
循著相同的邏輯,在臺灣內部,資本從早期即利用「由農轉工」過程所產生的剩餘農村勞動力,來「外部化」其生產成本。所謂「剩餘農村勞動力」包含漢人社會、也包含原住民社會的「剩餘」人力。
為何稱之為「剩餘」?在漢人農村社會,「剩餘」勞動力來自在國家政策主導下的由農轉工的經濟過程,農村機械化與使用化學農藥及肥料,「提高」了生產效率而所產生的「剩餘」勞動力;在原住民社會,「剩餘」勞動力則產生在原住民社會面對初具雛形、以水稻為主的「定耕農業」在市場競爭下解體,以及由政策主導的「原住民社會改造運動」,將原住民社會納入市場經濟所產生對貨幣經濟的依賴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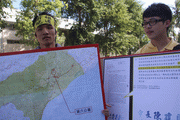
最令族人感到疑惑的是,為什麼一紙公文、一個行政命令就可以改變我們賴以為生的一切? |
無論是資本對勞動力的剝削,或是資本將生產成本外部化,引起受壓迫者的反抗成為自然的結果。1970年代以來,臺灣原住民社會的反體制運動開始明顯地被矚目。早期有原住民權益促進會、還我土地運動、正名等,屬政治抗爭的場域中進行的「運動」;近期則有關原住民自治及其在憲法中位階的討論(自治)、原住民傳統智慧與智慧財產權的討論、原住民傳統領域調查、原住民與政府對自然資源建立「共管」的運作模式、原住民傳統慣習法制化等,從學術調查與立法保障的雙重實踐,來實現早期政治抗爭的成果。當然,這些發展也反證臺灣資本主義體制發展過程中,原住民族社會對其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各層面受到擠壓,在土地權、人權、文化、信仰等各方面的失落。
「反體系運動」雖對資本主義深化作出反應,但是,其所反仍不免受到資本主義體制本身的邏輯限制,乃至於反體系運動的場域、遊戲規則,都未免染著資本主義邏輯的色彩。例如對「原住民傳統生態智慧」的呼籲,認為傳統原住民生態知識符合若干現代生態科學的原則而有「保育」的效果,未能完全跳脫現代與資本主義共生的西方「科學主義」的窠臼;在國家主導以「文化」、「景觀」「生態」的資源,發展「民族經濟」的運動中,也有淪為「市場商品」而進一步被「資本」所壟斷、剝削的危險。

如何許原住民下一代一個不受擠壓的未來,一個不受壟斷與剝削的集體生存權益?在爭取資本與市場的同時,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面向。 |
由「還我土地」運動而開展出的「原住民傳統領域」的調查,受現代國家個人主義市場經濟的「財產權」觀念的影響,忽略前資本主義社會重視集體性、由生活實踐產生的流動性領域疆界的歷史真實,而導致原住民各部落之間關於「傳統領域」範圍的爭議不斷。
又如在近年「原住民習慣法法制化」的討論中,由於缺乏原住民習慣法與現代國家體制下的法制體系的比較,也對傳統原住民社會重集體、建立在「互酬」交換基礎上的另類「法制」精神,與現代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在以財產權為基礎、以市場為個人營為場域的法權體制相左,而一直無法具體落實。由於兩者的矛盾性,原住民社會建立在集體、共享的生活實踐的「法權」體系,恐怕也終將無法落實在以個人財產權為基礎的國家法權體系之中。
由這些例子,我們看到原住民的「反體系運動」有必要進一步釐清「傳統的」社會經濟體制與現代資本主義體制運作邏輯的根本差異以及此差異的社會基礎。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
本文亦發表於「史前館粉絲頁 」,歡迎分享討論! 」,歡迎分享討論!
▲TO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