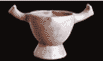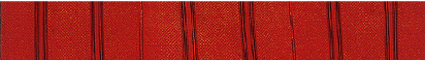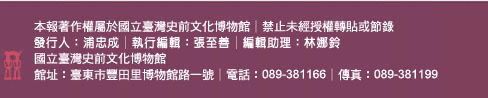豆花之祭meefo’na原本是距今約四、五百年前在阿里山鄒族特富野tfuya部落舉行的巫術性儀式,當時的部落領袖peongsi稱為niahosa(今漢姓梁、陳)﹔根據特富野部落的口傳材料,大洪水之後,原本在玉山patungkuonu躲避洪水的各個家族分別下山,尋找建立部落的地方,當時niahosa氏族先遷移到玉山西方今南投信義鄉和社溪一帶,經過相當久遠的時間,便南下穿越清水溪,到達曾文溪上游二支流繞經的河階台地----tfuya(特富野部落)。niahosa氏族進入特富野建立男子會所庫巴kuba,後來其男子出外巡遊狩獵時,發現其他氏族建立的聚落,niahosa氏族為了壯大部落,便陸續邀請yaisikana氏族(今之石家)、yatauyongana氏族(今之高家)、tosku氏族(今知杜家)、yavaiyaana氏族(今之汪家,現稱peongsi氏族),形成特富野部落組織的基本成員,這些家族在部落的mayasvi(瑪雅士比)祭典及收穫祭homeyaya時,仍然可以見到他們特殊的家族地位(註1)
。
由於niahosa氏族首先進入並建立男子會所,是部落名符其實的主人,加上其男丁眾多,因此除了擁有實際的領導管轄權威外,根據相關的口傳敘述材料,他們的行事相當專斷,對於部落其他家族的成員,經常暴力相向,有時會焚燒其他氏族擁有的土地獵場hupa,閒暇經常慫恿男丁從事獵人追逐野豬的扮演buafuzu(註2),造成重大的傷害。長時期受到欺壓,各家族雖有怨懟,卻因niahosa氏族人口眾多,也毫無對策。
豆花之祭就是niahosa氏族作為特富野部落主人時進行的一種農作儀式﹔時間在每年粟米秋收之祭。傳統的粟收穫祭進行數天後(通常是第七至第八日),部落男丁要進行集體狩獵miyokai
,此時前述五大家族會派出五位長老擔任社口(部落上方,朝東方)守候工作ak’e
tutun’ava(社口守候老人),五位老人夜宿二日後,集體狩獵的隊伍將要返回部落,老人於社口打陀螺以求獵隊順利。獵隊到達社口時,婦女早已攜米糕ufi等候,獵者分別取米糕小塊進行奠祭su’tu,再進食。豆花之祭此時上場。依據部落耆老的記憶及口述,參照相關的文獻,此一巫術儀式是在社口平坦處進行,由部落主人令一男子仰臥地上,揭護陰布,露陽具,再令少女持藤豆fo’na花置於男子陽具上,以下陰擦落豆花五回,儀式即成。這樣的儀式屬於模擬的巫術,是祈求粟作豐收的儀式作為,在許多民族可以找到類似的巫術行為。譬如在初春之祭,作物新植,男女成雙入林蔭處交好,期望以兩性交好與生殖的行為,帶來農耕的豐盛的收穫。【周易繫辭】說:「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及【詩經小雅】「甫田」記述上古人迎御田祖,祈求雨水,盼望穀物豐收,人丁興旺,而所謂「御田祖」就是在田地播種時,以男女交合的儀式,女陰象徵田地,男精象徵種子,男女性交譬喻「播種」、「耕耨」,以祈求豐收,說的是相同的概念。昔日特富野niahosa氏族實施的這類模擬巫術儀式,已經不是真正的性交行為,僅是扮演與模擬,更早時期可能存有類似「御田祖」的方式,即進行男女交媾的行為,但是隨著知識文明的增進,實際的交媾轉變而為陰陽接觸儀式的扮演,但是現在能夠掌握的文獻資料,都無法證實它是否曾經存在。擦落藤豆花五回,也有特殊的意義,這類藤豆可以栽植於任何地方,不拘地質的肥瘠,一株可以繁衍成交纏重疊的蔓叢,族人隨意種於路旁,無須刻意照料,它的蔓藤可以覆蓋茅草,攀爬樹木,秋收正是這種藤豆開花的時節,取其花大概是源於主觀認知這種植物強韌而旺盛的生命。擦落藤豆白花五回,亦有特殊的宗教意涵,五的數字是鄒族特富野文化內涵中特殊的數字,能讓人神之間產生直接的呼應與作用(註3)*。由此以觀,豆花之祭最核心的意義在於祈求粟米的豐收,是典型的農作巫術儀式。
特富野niahosa氏族最後一次實施豆花之祭的時間距今應該已經超過四百多年,當時現在部落領袖家族peongsi尚未取代niahosa而獲得部落主人地位,當時南方的小社taptuana(今達德安社)仍屬於特富野部落,很可能當時被挑選的少女就住在達德安小社,所以她受辱後會偕同數位姊妹縱身跳入該小社稍北面向曾文溪現稱mamespingana(女人之崖)的崖谷。當時之所以會發生悲劇,起因被挑選的男子是該少女素來極為厭惡的男子,因此少女拒絕參與配合,被挑選的男子覺得受到侮辱,便強拉少女進行儀式,並在在儀式中羞辱少女,事後少女悲憤不已,返家哭訴於數姊妹後,便決定一起自盡。造成這樣的悲劇之後,部落就決定停止舉行這樣的儀式迄今。後來特富野部落內部對於niahosa氏族許多獨斷霸道的作為不滿,此時peongsi氏族適巧出現渾名ak’e
yam’um’m’a(長毛祖父),他向niahosa氏族的眾男丁挑戰,讓niahosa氏族屈服於他的勇武,並讓出部落的領導權,從此以後,特富野部落的peongsi(部落領袖)就在這個家族產生迄今。
文化的承續有它主客觀的因素及條件,如果分析豆花之祭由可能是男女真正交媾以禱求粟作豐收,進而採取模擬扮演的型態,終而因為實施過程中產生人為非理性作為導致悲劇發生而無法延續,文化功能論者的觀點在此獲得相當程度的驗證,文化的形式與內涵必須要對於創造和維持它的群體發生積極的作用,這樣的文化才可能獲得延續,因此豆花之祭在悲劇發生之後已然壽終正寢,現在鄒族特富野部落的領導權已經易主,粟作已非主要農作,人們對於豐產的追求已經捨棄巫術思維和途徑,農藥肥料和生態耕作也完全可以取代模擬與扮演帶來的主觀感知效用,傳統的巫術或宗教思維已經在新式教育和西方宗教進入部落後,產生質變後的效應絕對無法再引起部落原有的崇敬心思,「meefo’na
ta niahosa」(niahosa 氏族的豆花之祭)在阿里山鄒族部落的社會語言詮釋意涵,其實具有很明顯的嘲諷意味,在傳統的文化環境、宗教氣氛與產業需求無一具備的情況下,鄒族的族人要將已經遭到棄覺的巫術性儀式找回來,而且這種儀式過去僅在特富野部落實施,由niahosa氏族主導,如今由地方政府匯集資源,打算大規模辦理,而且在鄉政首長個人任意的扭曲其原本的文化意義
,確實令人覺得有時空錯置的感受。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