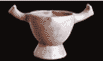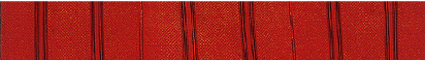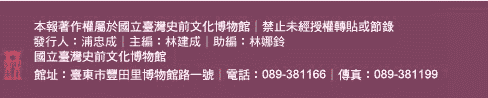五、近代排灣群與巴蘭舊社
近代北排灣族的民族誌材料提供給我們一個思考巴蘭考古資料的方向。站在一個考古學研究調查的角度,我們可以將以上的民族誌資料反轉過來。首先,我們假設經過時間的過程(例居址被棄置,舊來義目前即已進入這個過程),P村與來義舊社成為考古調查的對象,如果這個情況發生,民族誌所載北排灣族家屋內的行為模式所遺留的物質文化,則有可能變成考古發掘中出土的資料,正如今日考古發掘中我們所見到巴蘭遺址的考古資料一般。正如在以上的討論中所隱含的,在P村與舊來義村,調查者對於兩村的物質遺留資料的解釋,必須透過對兩村人的社會組織及文化觀念的瞭解才能建立,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對於巴蘭考古資料的解釋。
巴蘭遺址的考古資料顯現與近代排灣群民族誌資料之間有明顯的類源關係,以這兩組資料作類比的討論有更具體、進一步的意義。首先,如果我們假設近代排灣群文化的前身是以巴蘭遺址所代表的社會與文化,後者如何演變成為前者的問題,似乎是無法具體解答的。這是因為基本上沒有文字或口傳資料的輔助,歷史過程中所發生的轉變是無法被研究者知道的。這正如在前引P村的例子中,如果沒有耆老的口述,研究者不可能知道日本人有禁止室內葬的措施、而研究者也不可能知道由曲肢葬改變成仰身直肢葬的歷史背景是什麼。然而,研究者縱或無法知道具體的歷史事件,但研究者對於轉變(或延續)仍可從整體的觀察上加以著墨。例如,在P村墓葬形式的轉變中,不變的是促成這個轉變方向的、在其底層的文化觀念,也就是有關「家屋」的文化觀念與社會關係叢結。第二,承接以上,雖然巴蘭遺址的資料中缺乏的是與P村類似的單一歷史事件的資料,然而,由出土的房屋及墓葬,我們可以合理地假設:1)家屋及墓葬為外顯的物質遺留;2)此外顯的物質遺留有其文化與社會的基礎;3)此文化與社會的基礎,「極可能」也與P村和舊來義有相類似,以及可能有傳承與轉化的關係。
在這三個假設之上,我們對於如何檢視巴蘭遺址的考古資料的問題,或許可以有一些新的思考方向。簡而言之,如果我們視巴蘭遺址出土的家屋結構為記憶的載體,在大方向上,我們可以由這個觀點來看這個載體所記憶的是什麼?如果我們進一步辨別巴蘭遺址的記憶載體與近代排灣群的異同,我們可能可以藉由詳細的發掘資料,來辨識此異同之處是否有相同的社會文化因素在作用。另外,我們也可以由同樣的觀點來切入巴蘭考古資料本身所呈現的普同形式與變異現象。經由這兩個面向切入巴蘭遺址與近代排灣族的資料作比較性的研究,我們有可能可以對隱藏在巴蘭遺址考古資料背後的社會的動力產生一些可能的假設與可能的解釋,這些是假設與解釋是開放性的,它可以(也必須)透過遺址出土資料加以檢驗,也可以被進一步的研究所改進。另而言之,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雖然無法知道在巴蘭遺址發生過的單一歷史事件和這些事件所造成的影響,但由以上所提的假設和比較研究,我們仍可對長時間中,巴蘭遺址以及近代排灣群文化與社會在結構上所發生的大的變化,以及不變的部分進行觀察,並或許提出一些造成這些結構性的持續與變遷的假說與看法。
六、 結論
在巴蘭遺址的考古資料中,其家屋與墓葬的型制,以及其出土的物質文化與近代排灣群有極相似的面貌。這個相似性建議了巴蘭舊社與近代排灣群可能有一定的傳承關係。在討論台灣史前住民與近代原住民族群的研究領域中,巴蘭遺址的材料建議了一些可能性。但筆者認為這個可能性並不指向直接的對應關係,而應該是指向考古學研究中社會理論的建構。筆者認為,因為歷史材料(包括口傳與文字)的缺如,研究者將無法建立直接的傳承關係。但是,由如果基於社會理論的假設、對於考古資料的發掘與分析以及比較性的研究,對於巴蘭遺址社會動力的理論建構是有可能的。
以上的這些看法,多少也初步回應了本文在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首先,有關考古遺址與「族群」、史前文化與近代原住民社會是否存在單線、直接對應的關係,以及「假設性的穩定狀態」等的問題。筆者認為一個所謂「文化」或「社會」指的是在一個時間階段中存在的「相對穩定」的「社會文化體」,其中包括物質的環境與人的關係,以及其中的文化觀念。考古遺址所表徵的是這個社會實體的一個例子。因此,考古遺址是否代表一個「族群」或「民族」,在上述的定義之下,答案是肯定的,但更要注意的是,考古遺址並不單一存在,其與其他遺址在時間與空間上的脈絡關係也是構成該所謂「遺址」的一部份(參閱Kristiansen
and Larsson, 2005)。第二點,「社會」或「文化」或「族群」、「民族」之所以被認為處在「相對穩定」的狀態,是因為在穩定中,變化的因子亦同時隱含在其中,它穩定與變化的基礎繫於其中的人的社會實踐。這個看法也同時打破早期人類學理論中對「社會」的本質論的假設。第三點,史前與近代原住民族群單線、直接對應的關係是否存在,是乎是難以考據的問題,從建構考古學社會理論以及解釋遺址現象的角度來看,筆者初步還沒有想到,在這個討論範圍內,建立這個直接的對應關係有何作用?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