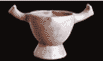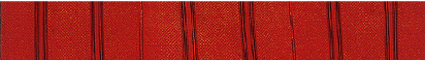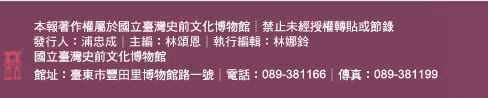上課過程中,我也從文山的課後心得獲得許多激勵。例如他提到每一次的課程都讓他有不同的感動與啟發,讓他有股衝動想要把這些內容分享給部落,讓族人可以藉由不同的工藝作品認識不同的族群文化,不僅去發展部落同時也強化對自己文化的價值與信念。於是我問文山,願不願意嘗試看看跟館方一起合作,把這些他所學到的東西,以巡迴展的方式帶回去跟部落的人分享。文山有個重要的特質就是利他性格,會為了群體的利益去努力,而不會在意自己所要擔負的犧牲與重擔有多大。部落策展人首要就是要找到這樣不會去計較利益、只會在意是否為地方帶來祝福的人,於是我們有了一個很好的共事意念的開始。
當纖維創作培訓班準備以「用手去找‧新纖事」纖維創作特展的方式於本館展出時,我們已經開始構想,來義鄉這檔巡迴展要如何呈現?文山提出的是,他想要結合部落的工藝家,以他們的作品作為當地展出時跟館方成果展一起展覽的主軸。這樣的構想非常好,畢竟,來自於外面的作品一旦在展覽結束之後,都是與當地無關買空賣空的操作,唯有結合部落性的熟悉事物,那樣從自身而來的脈絡才會讓當地族人產生親切的連結感,而對所有展出的事物感到興趣。
後來文山也就他對部落事務的觀察以及就博物館化操作的經驗,提出部落需要有一份介紹部落的掛圖設計以及部落導覽地圖的DM,後來又加上為參展工藝家製作帶有文字介紹與作品圖片的人形立牌輸出,這些剛好都是博物館介面可以發揮的項目。很顯然的,今天部落不可能自行支出數十萬的開銷花在展覽的基礎工作,例如輸出、印刷、臺座的設計製作等,然而這都是博物館熟悉的操作而可以就形式上進行協力,由部落提供本質內容,這是兩造之間可以相輔相成的合作方式。
於是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朝向彼此提出需求與看法、雙方協調與互補的模式去進行,成為部落與博物館這兩個介面各自聯繫與匯整的窗口。然而在這過程中並不表示,我跟文山兩方之間就沒有所謂溝通上的問題。我對他的落差,來自於我對部落所習慣的思維、生態、動員模式與處理方式的不夠敏感而產生問題;而他對我的落差,則在於他與族人對策展介面陌生而提出異於博物館設定培力模式所帶來的意見,因此在過程中,我們都有需要不斷一往一來溝通、轉圜、修正、調整的地方。
在這個多磨折的過程裡,確實,讓我看到了「萬事互相效力,叫愛部落/愛博物館的人得益處。」我想在這一點上,文山跟我都有很大的受益與學習。當我在當地看到文山以「部落策展人」這個頭銜發文通知族人前來開會的通知單、看到開展邀請卡上打出這些字樣,我的心是欣喜的,samiyayan(很美)、bulay(漂亮)這稱呼,但我也忍不住提醒他,這個身分所會面臨與承受的種種狀況。那簡短有力的五個字道出的是他在這個展覽所擔任的重責大任,含納所有的甜蜜與不快、陶醉與受挫,就像策展人與工友其實是兩面一體的角色,什麼都要做什麼都不奇怪、什麼都要擔什麼都不誇張。我知道文山在這次巡迴展的角色一定不會是「配合」館方作業流程的下線工或隱形人,而是具有獨立意識在操盤承擔的策展人,要將這一切經驗轉化為部落未來對博物館介面操作的有力累積。
重新再看一次招生訊息辦理巡迴展的文字,最後一句話我這麼寫道:「你願意進一步接受這項挑戰嗎?說不定史前館跟你的部落有可能從此擦撞出未知的火花呢!」結論是不只火花,我跟文山還二級燙傷哩,因為我們都在許多資源、人力與意識還沒陸陸續續到位的情況下就開始玩火,自焚後果之猛烈之精采可想而知。但是這次的經驗都讓我們進入願意更加走火入魔的練功境界,想把我們辛苦的、快樂的、活該的、覺得有意義的經驗落實在往後操作上的擴散,希望能夠有更多人感受到,其實部落與博物館之間還有很多想像的實踐可以發生、可以創造,只要雙方願意,過程中一定都有可以成長學習的益處。至於這些創傷往後如何復健,就學習以無畏的心安然交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