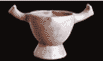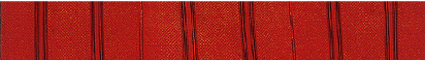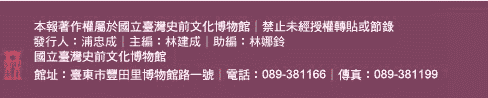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策展過程對部落對博物館而言都是一種困惑。(陳文山攝) |
| |
「用手去找‧新纖事」纖維創作來義鄉巡迴展暨當地工藝聯展開展的早上七點半,我跟本館解說員李虹妮、志工鄭丞志,還賴在部落策展人陳文山(angusan)七佳村家裡的床上,很近很大聲的聽到這樣的廣播清楚地傳入耳膜:「(排灣語)~~各位村民早,今天,在南和部落,(排灣語)~~~~有展覽,『用手去找、找、找』………(排灣語)~~~下午兩點開幕,歡迎大家參觀。」過沒一會兒,更遠的空氣傳來另一個村子的廣播:「各位村民早,(排灣語)~~今天下午南和村的來義鄉文物館展覽開幕,(排灣語)~~~「用手去找‧新纖事」,歡迎大家參觀(排灣語)~~~。」一個很美的清晨,一段對族人而言是日常中再平凡不過的宣傳模式,但對館方工作人員而言卻是特別的開展通知,把我們兩個禮拜在當地所經歷異於博物館佈展與開展模式的體驗,做了一次很有意思的宣告。
一開始要到南和部落辦理巡迴展,身為館方這檔纖維展策展人的我對於部落策展模式還處於想像中的紙上作業,說是天真的策展人也不為過。哪曉得隨著佈展時程越近,與部落的接觸越形密切之後,才發現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首先發生的問題就是,對部落來說,一個展覽發生在部落,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所謂博物館模式的策展,對部落而言到底是什麼樣的過程與意義?當館員與志工第一次造訪部落進行場地探勘與當地族人意見探詢時,我們很天真的將重點放在丈量展場大小,卻忽略了族人對策展繁瑣事務的陌生。例如族人第一個提出的考量就是,開幕那天與展出週末期間希望能擺攤賣小吃、工藝品等,似乎展覽對族人已是一個現成的生成物,比較在意的是周邊具體的商機效益。這跟館方期待開展時間點之前能有一組人馬願意在過程中學習策展的想法完全搭不上邊。
然而對於當地如何真正形成一個可以與館員共同策展的團隊,這樣的鴻溝,即使是到了第二次到當地準備要進行解說教育訓練時,還是無法被彌補,於是館員與族人之間就策展意識上就形成很大的落差。例如當天來上解說訓練的族人多半是不諳國語的年長者,出現一下就離開的中青代,則多半處於觀望的態度,部落策展人猶如無頭蒼蠅般不斷找人來聽說明會,希望族人能更深刻參與時間點之前的佈展作業……
在面臨工作團隊欠缺的情況下,館員不得不臨時變更工作計畫,猶如跑江湖的郎中,對著不知道到底誰才是潛在的協助工作者,一場又一場地賣著膏藥兀自解釋著「今天來到貴寶地」。一位參展者小孩的神情,大概最能傳達雙方這種認知上的落差:當我們帶著白布到處去拍參展者全身照好方便設計師的去背作業,這種專業置入的強迫性操作給部落帶來的,可能不只是好奇與困惑,或許還有更多的不解與攪擾。
事實上這些對館員來說也是需要反省的。身為館方工作人員,我們很習以為常的認為,辦展覽就是這樣反正那樣的流程,因此很容易以既有的模式想當然爾的方式比照辦理,然而這個介面對部落而言卻是未曾擁有的經驗值。畢竟就算對於曾經參展過的族人來說,他們所擁有的參展經驗多半停留在把作品提供出去、等候接獲邀請卡通知的層次。於是初期在與當地部落策展人溝通時,我們還流於口頭提醒的事務交代,卻忽略了對方此時最需要的是一份文字化的完全策展攻陷秘笈,好讓他可以進入按部就班的工作狀態。此外館員也一廂情願地忽略了地方的行政生態,以為到部落辦展就像在館方一樣可以獲得行政資源的支持,事實上不管在鄉、村或社區發展協會方面,例如年度預算或行政程序倫理等問題都不是那麼簡單。
而當我們還帶著博物館規格的腦袋想要到部落進行類似博物館化的操作,所面臨的現實問題也往往不在我們的經驗值當中。博物館很容易採用熟悉的制式化流程去做一貫的操作,例如特展一定會出現的精美海報、多彩旗幟等這類出現在都會友館與重點街道的模式,我們也把這一套移植到部落。然而對部落而言,若要達到部落化最實際的宣傳效果,最直接的仍是大字鮮明的雙色布條,加上無所不在最具穿透力的村長廣播。這種感覺很像當年美國獨立戰爭,英軍慣以排排前進自以為堂皇射擊的方式作戰,冷不防卻被採用當地原住民突襲方式作戰的民兵給撂倒那樣,是必須因應當地場域情勢加以調整才有辦法打下去的作戰法。
另一個介面則是展品上架的操作,在部落的上架法絕對無法比照館內模式進行,同時也要將場地的限制轉化為有利的條件。例如我們就把通往二樓的樓梯用布料封起來,利用階梯的段差擺上板雕作品,看起來就有專門打造的台座效果。我們笑說大凡能被博物館典藏的展品在館內上架時,絕對少不了專業典藏工作人員極為細緻縝密的標準流程上架作業,以及各式的監測檢控儀器設備,場景之慎重猶如御醫幫皇后接生皇太子一樣。但是以非典藏品的作品拉到部落跟當地作品一起展出,人力與情況完全不一樣,於是我們這組現湊人馬就像密醫帶著實習助手在接生一樣,只要生得出來,其他按照我們。換句話說,我們以野戰部隊的作法處於一種趨近想像式的類專業操作,但在效果上也要盡力呈現出夠專業的模樣,這種見招拆招的打法就很具挑戰性與趣味性。
儘管是這般土法煉鋼的模式,不置可否還是產生很多創意的火花。例如當我們遇到月桃蓆作品上架的問題,手上所擁有的不過是文具店買來的彩色大頭釘,於是在當地族人大發奇想的建議下,就把土黃色封箱膠帶剪一小塊貼在圖釘上,企圖在相近的顏色上以魚目混珠的方式讓觀眾看不出這蓆子到底是怎麼固定的。結果在昏暗柔美的投射燈作假下,竟也出現再好不過的效果。另外一件大型板雕則是在找不到夠寬的台座可以固定之下,乾脆就拿兩張摺疊鐵椅,將免洗筷折斷沿著作品邊緣插在椅面小圓孔,再舖上米白色的布料當底,既達到保護作品的止滑目的,也盡可能達到展現作品的效果。
這樣的過程,事實上也對部落的人產生啟發作用,原來作品上架沒有想像中的困難嘛,只要可以達到效果,都可以嘗試任何方式去找出可行的模式,而且更符合當地現有材料與工作方法的條件。於是,一檔在博物館花費百萬等級的展覽,很可能到了部落操作時,只能有少許經費支應佈展材料費與雜支去呈現,但在本質上卻也同樣企圖藉由展覽達到溝通、分享與交流的目的,而且擁有更多當地人參與建造的過程,成為一起品味流汗、頭痛、嘻鬧、tjapuljatau(大家乾杯)的歷程。這樣的佈展方式,是絕對不同於館方與廠商之間純就專業、合約與公文往返要求對方做到最好的形式,更接近地方上人與人之間革命情感的親密流動。而這也是博物館想與部落藉由展覽操作來達到社區營造培力的目的,是需要雙方共同努力的夥伴關係。
於是,對於一個建館完成之後,除了村辦公室與托兒所之外從未發生過展覽的文物館,當展覽就近就地發生在部落內部,我們看到的是什麼?
是開幕式村長致詞說,想不到部落老人家做出來的東西可以用這種方式讓大家看到,讓他們地方對於用這種方式去發展文化感到新奇與肯定;是年輕族人對於親戚的創作力大感驚嘆,想不到平常到對方家走動也不曾注意的東西,竟然在文物館展場看起來好棒,讓他們更佩服更尊重老人家的智慧;是小孩子光著腳跳進來,興奮地對同學說看哪是你爸爸的木雕耶那樣的與有榮焉;是vuvu(長輩)對於日常熟悉物件轉化於此一場域的分享而感到竊喜,滔滔說起他對該物件的敘事記憶;也是先前來不及意識到要參加展覽的族人,終於對展覽的成形產生具體的認識而希望參展,然而在時間點與展場配置上已經讓我們不得不拒絕沒有脈絡而突如其來的作品……部落的人在這次的經驗值之下,開始對展覽有了不再是遙想的接觸,可以是身邊更部落性的具體存在感與親近感。
然而對於出現在部落的展覽,更嚴苛的考驗還在開幕式之後。不同於博物館總有車潮往來的人數進進出出,在部落的展出很可能人數最多的時候僅出現在開幕當天的萬頭鑽動,一如一般文物館落成的盛況,接下來就要面臨獨守空閨盼不到人的焦躁難耐。當報紙與電視的開幕報導如花籃凋萎般成為昨日黃花後,還有多少人能記得這個展覽會在當地展出兩個月?發文給鄉公所、文化局轉知相關藝文團體前來參觀是一種操作後證明有效的方式,然而對於這樣的預期目標群眾,他們會產生足夠的動機聞風而來嗎?還有很多的不確定性,都還在發生。
儘管如此,我們這支野戰部隊還是只能說,那美好的一仗我們已經打過,就像看著櫻花紛飛始終堅持初衷的武士一樣。對部落策展人而言,當初想要聯合村內工藝家把部落手工藝推展出來分享的目的已經達成,而且正要發酵;而對博物館當初辦巡迴展的期許,在於與部落就博物館與展覽介面做培力與陪伴的連結也已實現,同時也朝向更長程的發展在醞釀。未來我們期待的是藉由更多經驗值的累積,提升戰鬥值的能量,好與更多部落一起合作,共同發掘展覽的迷人之處及其在本質操作上所能達到猶如社會運動般的最大值。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文中族語拼音感謝久拉卡拉久部落文化推展協會理事長
valjeluk.katjadrpan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