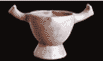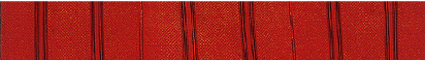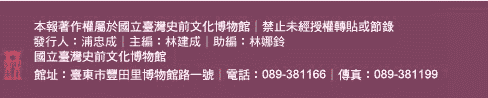高一生傳記 |
2003年,史前館策劃推出「回憶父親的歌:陳實、高一生與陸森寶的音樂故事」展,以音樂創作者的角度,帶出他們的音樂與人生。館內一些研究人員與觀眾有兩種反應,讓我特別有感覺、有感觸。一是問號,他、他們是誰?二是驚嘆號,故事感人!這兩種反應,反映出博物館展示原住民文化的侷限與潛力。
他、他們是誰?反映了原住民缺少歷史人物,很少從歷史人物角度去閱讀原住民,以及背後所反映的時代背景。感動或感人!在於讓我看見在歷史上留名的人物,他們的精采生命,所產生的超越時空的感染力,具有一種共通的溝通力量,是不分族群與古今中外的。
長久以來,原住民的文化、社會問題,甚至是原住民的心理傷痕,被整體化而忽略個體差異;抽象化、理論化與數字化,因而失去血肉、失去具體的生命經驗,難以讓人體會、很難觸動人心。
1991年,卑南族學者孫大川即語重心長的指出,人類學的原住民標本化再現方式,猶如醫生之解剖屍體,無法幫助我們認識一個人的情感、處境與希望。
解剖,意味著剖開軀體,研究各器官、骨骼及筋肉等結構型態。科學的基礎工作與研究方法,是敞開知識大門的一把重要鑰匙。然而,在博物館強有力的單一價值長期影響與模塑下,原住民成為一個客體,知識體系。漸漸地,我們眼中看不到一個完整人,只看到從身體上一塊塊被分割、肢解下來的差異文化特徵。原住民正一吋吋解體、離開了真實的生命。
當原住民文化、一個人、一個生命,成為抽象知識後,如何揭開抽象的學術理論與知識系統,還原具體的生命原像,如何從族群文化釋放個人記憶,反而成了這個時代的課題。
原住民的歷史仍是模糊的,更遑論歷史人物。《政治與文藝交纏的生命:高山自治先覺者高一生傳記》,是第一本深入挖掘的原住民歷史人物傳記。由同是鄒族人的學者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先生,累積前人研究,透過高一生的創作歌曲、獄中書信、黑白照片,以及作者一個個文字的縫補織羅,讓高一生(1908-1954)在世人的眼前鮮明起來。
作者因與高一生同血緣(同族同氏族)的關懷,以及同是原住民知識份子的同理,往返兩個時空之間,有著更深刻的感受。瞪著高一生槍決前的檔案照片,按耐住巨大的衝擊與悲傷,揣想高一生瀕臨死亡的心境,穿越死亡,試圖將不滅的靈魂帶回來!帶到這個時空與讀者相遇--一個有血有肉的身軀,一個有思想的靈魂,一個有情感的心靈,而不是一個簡化的、與我不同的差異民族性,亦不是一個遙遠的異國想像。
從高一生的傳記,讓我們看到當時鄒族的歷史背景與時代情緒;從高一生的歌曲,讓我們看到普世的人性與價值,對愛情、親情的不捨與珍視;從高一生的書信,讓我們看到舊殖民時代下一個原住民知識份子的使命、理想與處境;從高一生最後倉促寫下短短幾行字的遺書,讓我們看到當人看盡一切後,追求最簡單的幸福注定永不可能實現的椎心之痛與遺憾。
一個為人夫,為人父,為鄒族傳統部落中最早受過近代新式教育的現代知識份子,為殖民國家行政體系下的官員,多重角色的交雜。看到族群差異,亦看到了人性。使我們深刻體會到個體生命的豐富與複雜,亦反射出這個社會(包括博物館)以一個部落、一個族觀看與再現原住民的侷限。
時代的政治現實,讓我們看到了歷史悲劇;時代的深刻反省,讓我們看到了悲劇人物的生命美學形式,一個背負叛亂罪名的政治犯,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受難者,翻案成時代的先覺者。高一生在四十七歲正待發揮的年紀殞落,但卻成就了一種感染人心的悲壯生命美學形式與巨大力量,也為台灣歷史、原住民歷史、鄒族歷史,烙印下一記重重的歷史印記。
時隔半個世紀後,高一生個人生命所創造出的新力量,仍能超越時空、穿越死亡,成為現代不分原漢共同的歷史遺產,甚至對於許多缺乏清楚歷史與人生軌道的新一代原住民青年來說,高一生是一個重要的人生參考座標,甚至是,歷史典範。
參考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