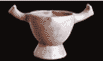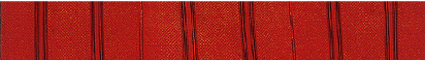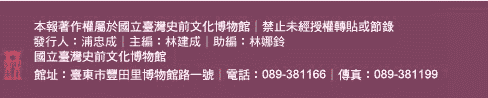四、近代排灣群的民族誌資料
透過日據時代民族誌記錄者,以及1960年代以來對排灣群研究者的研究,我們對近代排灣群社會文化特性已有一定程度的瞭解(有關兩族的研究文獻極為豐富,參閱傅君
2001, 頁13-31的文獻整理與討論)。大致而言,除去地域間的差異性之外,近代所謂排灣、魯凱二族社會有以下的特徵:兩族是以「家」為核心,外拓為區域性的親族組織社會;在政治型態上,此親族組織表現為部落內的「領主」(頭目)與「屬民」(貴族、平民)的關係,以及部落與部落間的主從關係。無論是在部落內或部落與部落之間,其政治關係透過親屬間的階序關係來運作,而非透過現代國家的權威模式運作。親屬間的階序關係的文化意識型態基礎建立在「長嗣」優先、「餘嗣」從之的觀念與實踐之上,而此文化意識型態又以其宗教信仰中「靈力」(legum)的觀念為基礎。兩族的社會組織與文化觀念最具體地表現在「家屋」的實體空間以及其中的生活實踐當中,前者包括室內葬的葬俗;後者包括長嗣承家、餘嗣分出、回歸本家安葬等習俗。
從蔣斌、李靜怡(1995)和蔣斌(1999)對排灣族家屋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看到排灣族「家屋」的實體空間所隱含社會文化意涵。在分別以屏東縣來義鄉來義舊社與屏東縣P村兩地為田野材料的報告中,研究者討論北排灣群社會中,有關「家」的組織型態、運作、社會再生產模式、以及其文化意識型態的基礎。在蔣斌、李靜怡(1995)文中,作者從家屋的實體空間配置、以及排灣族的兩性與同胞兩種關係如何透過在家屋中實踐出來的生命儀禮(生育、婚姻、喪葬),來討論家屋在排灣族社會中社會生產與在生產的表徵性意涵。作者認為,該族的兩性關係具體地表現在家屋空間在性別上的區隔,也表現在家屋的生活實踐當中。而在一家屋之中,兩性的合作構成家屋的延續與興旺。同時,對於一個「家屋」而言,婚入者(無論男女)在死後,皆回歸原本出生之家安葬。另外,家屋內的同胞關係,表現在長嗣、餘嗣、本家、分家的物質與精神面的交換關係上。簡言之,在長嗣承家餘嗣分出的社會實踐過程中,家中的長嗣幫助餘嗣另立家屋,而餘嗣則對「本家」在生時有物質的回報,在死後則以其軀體歸葬、回報本家。正如作者所言,作為一個」「『排灣族傳統文化』最初級且最方便的指標」(同上引,頁167),「家屋」是一個「傳遞排灣族文化對宇宙與社會的知識」的最具表徵性的實體物(見圖3、圖4;另見下引蔣斌,
1999)。

圖3:近代北排灣傳統家屋平面圖(引自巴伐伐龍,
n.d.) |

圖4:近代北排灣族家屋配置圖(引自蔣斌、李靜怡1995:196)
|
換言之,作為一個族群與社會的文化與歷史記憶載體而言,在排灣族(也包括魯凱族以及不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的台灣其他原住民族群),「家屋」可以被視為一個社會記憶的機制。根據上所引的研究結果,在本文討論的範圍內,一個家屋的生命過程中,有以下的幾個面相值得我們注意:
1. 在家屋中的人口的流動與留置:新生、移出(餘嗣分出)、移入(婚入)以及死亡(墓葬);
2. 物質的生產與流動:與人口流動與留置相關,包括小米、生產工具、建材、貴重物品如琉璃珠、陶器以及人的身體(胎盤、臍帶、屍體)等等;
3. 家屋的空間配置:包括依性別、世俗/神聖區分的空間;
4. 另外,最重要的是,左右這些人口及物質流動的文化觀念如:對長嗣重視的觀念、性別的區分、以及前二者的基礎──「靈力」觀念。
在蔣斌(1999)一文中,作者透過對P村排灣族名制以及墓葬習俗的討論,來看這兩種社會記憶的機制如何構成排灣族社會不明顯的「中心型社會」之特質。在本文中,作者亦從另一個角度,為討論家屋在排灣族社會實踐在中的意涵提供了一些素材。
在該研究中,民族誌材料提供我們以下的意象:在P村,排灣族人採用一種自雙系(父、母)親族祖輩中為新生兒取名的制度。因此,新生兒的名字一方面代表其人本身,也承載著對雙邊親族的歷史記憶。這個歷史記憶,透過人死後歸葬于本家的葬俗,最終則被保存在歷史記憶最終的載體──墓葬之中。
另外,在P村,日據時期起禁止室內葬,由而村內的喪葬方式起了一些變化。根據蔣斌的記載,這個變化包括:1)在日據時期,在型制上沒有太大的變化,僅將將墓穴移到室外
;2)在1960年代,有些經濟能力較佳的家族,加入以大水甕裝載屍體的喪葬元素;3)1960年代,因為要等親友聚集追悼,有牧師倡議仰身直肢的葬式,以免需用蠻力彎曲死者肢體,這個提議廣為大家接受採用,而以往屈肢葬的葬式以及葬穴的型狀也因而跟著變化;4)1970年代,因為室外墓地不敷使用,因此,墓穴從以往的單體型變化為複體型,而墓穴的型狀也附加了一個空間,以容納腐朽的屍骨。(見圖5、圖6)

圖5:北排灣族墓葬型制變化(1)(引自蔣斌1999:393)
|

圖6:北排灣族墓葬型制變化(2)(引自蔣斌1999:395)
|
值得注意的是,在蔣斌的描述中我們見到在短短五、六十年之間,以往室內葬的型制有相當大的轉變,然而,我們也看到在型制改變的內裡,在室外而建造屋頂模仿家屋的型制,而家族合穴的習俗也以擴大、變更葬穴的因應措施而保存下來。換言之,在P村,排灣族人喪葬的習俗因外在環境(政權干預、居民與外在社會經濟的接觸等)而改變的過程中,傳統關於家屋的文化觀念仍表現出相當強度的張力,左右著這些變化的方向。
綜合以上,在北排灣的社會裡,「家屋」是排灣族人歷史記憶的載體,在家屋內的行為模式(社會生產及再生產)是該族社會制度與文化觀念綜合表現的縮影。換言之,如果要瞭解北排灣族人在家屋內的行為模式,我們必須由其社會組織與文化觀念著手。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研究典藏組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