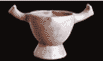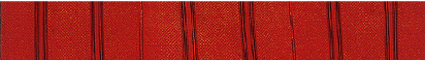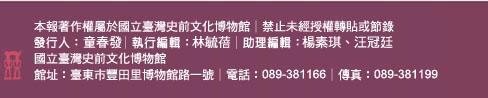|
小策展人失眠日記──大學醫院界的醫龍與我的1895,在壽豐 (1)迷霧
文 / 林頌恩 圖 / 張良澤教授
 七腳川事件非常令人動容的照片之一:引爆事件衝突的舊社東門入口
七腳川事件非常令人動容的照片之一:引爆事件衝突的舊社東門入口 |
 因為2008這一年是七腳川事件發生百週年,大家就這樣在開會上決定這個主題了。
因為2008這一年是七腳川事件發生百週年,大家就這樣在開會上決定這個主題了。 |
如果說,「Taupas‧日本軍─布農南洋軍伕回憶錄」,是一個極具挑戰的展覽;那麼「遺忘中重組─悲壯的七腳川(cikasuan)之戰」,就是一個挑戰度更高的展覽。到底……為什麼我老是康莊大道不走,偏是貪戀羊腸小徑自以為可以享盡不為人知的風光明媚,結果呢竟然陷入沒有方向的迷霧森林,一片愁雲慘霧。
「你真正的硬仗,會在壽豐。」2008年9月27日海端開展當天,馬田的話語有如巫師的預告,像是魑魅陰霧般糾纏著我。當下我就嘆了一口氣,深深了解他的明白。一來是團隊的欠缺,海端這邊起碼有五、六個文史工作者可以分擔工作事項,又有馬田這樣的在地人可以做設計。壽豐這邊如今我只知道部落策展人林燕萍和鄉公所承辦人鄭惠瑜技士兩位,他們先前的策展經驗多半以家政班成果展或藝術工作者作品展為主,因此對應於一個需要敘事結構的文史展覽作法,單憑他們兩個人要搞定所有大小事加上開幕式,那會很累人;二來是主題的年代久遠,光是距今五、六十年前南洋軍伕的海端這檔,就已經超難做了,開展前最後一個月好不容易才找到幾件真正日本時代的珍貴物件,讓人感到終於有東西可以像個展覽了;壽豐這場則是打一開始就知道,絕對不會有百年前那個時代的展品,那……難道又只能玩意識形態跟展場裝置的那種展覽了嗎?
當我們手上只有那45張來自張良澤教授與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提供的七腳川事件老照片圖檔時,最壞的打算就是展板輸出一張張照片,然後沿著牆面排一圈,看完以後謝謝參觀到此為止剩下沒有了。可是我又不甘心只有這樣,如果真的偏偏只能這樣的時候……。
一開始,燕萍對這個主題非常頭痛。原因是,我們原本以為當地文史工作者會在這個策展階段陸陸續續加進來協助文史調查,然後燕萍只要負責收稿寫展示文字稿就可以,結果這個重責大任卻落在她這位駐館規劃員以及另一位原民課約僱助理李玟慧身上。二、三十歲出頭的她們,沒有做過田野調查的經驗,加上年輕的她們母語程度還不夠好,要訪談耆老更是困難,於是兩個人都拉著自家媽媽前去找老人幫忙溝通,再把拍完的影帶給母語老師翻譯。這段過程,很像是開學前一晚全家出動在幫小孩子寫暑假作業那樣,兩代總動員用行動寫族語日記,是一場漫長的接力賽。
由於先前我把大部分時間都給了前一個戰場─海端布農族文物館,因此等到海端開展後,還要忙完一些稿約跟工作才能回魂,結果輪到壽豐這邊,大概只剩一個半月的時間可以開始投入。彼時燕萍雖然已經先給了我一部分訪談資料,但是老實說,當我看到她傳來的資料,跟達亥的幾乎沒有兩樣,意即不是我所期待先消化過再以自己主體意識寫出的展示文稿,於是我的心又開始滴血:「不會吧,難道,又是我要規劃展示文稿的邏輯順序?又是我要寫各塊展板引言?然後哪一塊展板放哪幾段訪談文字的意識,也是我要來決定跟擷取嗎?那這樣子的話還玩什麼呢?」
於是我還猶豫了一陣子,同時也鼓勵燕萍一定要自己來試試看,不管怎樣就是先寫寫看再說啦,不要連試著寫過的經驗都沒有。因此十月上旬那時,根據她訪談資料的內容我先做初步區塊切割,當時我只肯寫給她一份展示樣稿,規劃了一下區塊,說明大致可以怎樣用起承轉合這個概念,來針對七腳川事件做細部主題的發想或是展場裝置。至於要再繼續發展的文稿,我就回丟給她。因為這一次,我不願意像海端那場幫達亥那麼多,以致於剝奪部落策展人所必要經歷的學習過程,這樣子當他下一場策展如果沒有其他外力協助時,就沒辦法通過火盃的考驗這道關卡。所以我想賭賭看,這次不要一開始就立刻出招救火。
燕萍是那種做事按部就班的人,我跟她說什麼,她就跟著照做,果真她在月底前拼出了第一回初稿。然而除了必須多加修改的展覽源起可以使用之外,當我看著那團繼續混亂的展示初稿,很像是戰爭慌亂期間面對一群面目全非的屍首卻找不到自己親人的婦女那樣,明明應該要很熟悉卻完全還是理不出頭緒,翻來覆去卻找不到完整的面貌,切齒哀哭卻無法怨天,因為生活還是要繼續,展覽還是要做下去。
原本我以為只要陪著修稿就行了,看來我這位天真的偕同策展人還是必須出招。只是說這回我並沒有賭輸,因為這個試煉所帶來的操練,讓腦汁頻臨搾乾的燕萍學習到如何面對複雜的資料,怎樣順著主軸找出想要說給人家聽得懂的故事。如果說先前達亥還有很多沒做過的考驗,那麼燕萍都一樣一樣經歷過了。從她身上,我看到女性沉穩的承載力,非常的巨大、有力。可以跟這樣有潛力的策展人合作,真是我最大的慶幸與高興。
儘管如此,我還是對著這批不知該從何用起的初稿傷腦筋。再次跟我搭檔辦部落展覽的解說員李虹妮看過初稿以後更狠,直接用鉛筆在列印出來的文稿上寫說她看不下去。虹妮以解說員的角度站在觀眾立場上設想,她的意思是,就算是很部落型態的語法寫作沒有關係,那本來就很自然很OK,但是那個說故事的邏輯以及說出來的內容,還是要讓一般根本不懂七腳川事件的大眾,能夠在繞完一圈展場後起碼有個初步印象。因此以目前破碎的敘事結構呈現,觀眾是看不下去的。
虹妮以她的專業考量提醒我這個必要性,同時她也強調,這是我們館跟部落合辦的展覽,還是要做到夠水準才行。於是我要燕萍盡量把其他整理出來的訪談稿原貌寄過來,我還是得想辦法接手操刀,甚至是重新佈局,以燕萍跟七腳川後裔的角度去模擬跟思考各塊引言的撰寫,同時也不能忽略學術界已經出版整理過的內容……於是我們雙方都在各自的戰場上,學習面對如何從渾沌中殺出重圍。
然而對我而言,最大的痛苦並不在於對七腳川事件原本的陌生,而在於七腳川事件實在是太撲朔迷離了。對於事件發生的原委以及後續頭目如何處理與喪命的主觀認定,光是老人家講的話就有好幾種版本;至於舊部落所居地樣貌的客觀事實,居然也可以有兩、三種說法,這……一切都讓人霧煞煞。當我自己都看不懂、搞不定了,是要怎樣傳遞出至少不能是錯誤的訊息給觀眾呢?
說到這裡,我就不得不怨懟起阿桂(胡政桂)了。寫過「七腳川社(cikasuan)的研究」碩士論文的他是燕萍同學,早在半年前我們就力凹他來一起參加策展。因此一開始的選圖工作跟主題訂定,都是照著阿桂的意識走。他的想法非常棒,諸如「慘遭滅社的七腳川人真的『遺忘』此事了嗎?還是一直都在『遺忘』之中呢?」等等,阿桂的想法,讓我對於接下來的展覽走向有所期待。但是當他「原舞者」那邊的工作狂忙起來,而沒有辦法繼續參與時,我們可是背負著他定調出來的主題咬牙做下去的。對七腳川人而言是「遺忘中重組」,那對於我們做展覽的人來說可真是「破碎中重組」了!問題是,重組得出來嗎?是以何種觀點重組呢?我就像是在五里霧中跳傘的傘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著陸地會是在哪裡。
(本文作者為史前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