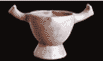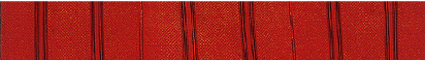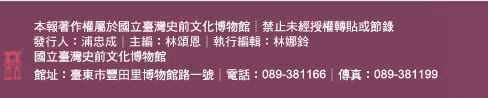1896年,為了不落西方殖民國家之後,東京帝大派了初學人類學的鳥居龍藏到台灣來進行原住民的調查,沒有受過正規人類學訓練的鳥居龍藏捨去傳統畫圖的方式,而以當時剛發展出來的照相來作圖像紀錄。沈重的照相器材及玻璃底片,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的臺灣原住民留下了珍貴的紀錄;年之後,鳥居龍藏第四次踏查的助手森丑之助在臨時臺灣舊慣調查會的資助下也深入臺灣原住民居住區域,拍攝了大量照片,出版了「臺灣蕃族圖譜」,是臺灣博物館展示或是相關出版品主要的舊照片來源,具體化也模塑了傳統臺灣原住民的想像。
也許「豬」從來不曾是這些攝影者拍攝的主體,但從老照片中仍可以重建部份當年臺灣原住民與豬之間的關係。由所收集照片來看,當時豬與臺灣原住民之間的關係有兩種:(一)豬是獵物;(二)豬是家畜。
從與狩獵有關的照片可以看出當時臺灣原住民使用的獵具有弓箭(圖一)、矛頭形狀不同的矛(圖二)、獵槍(圖三、四),而且獵槍的形式不只一種,圖三出自臺灣蕃族圖譜,森丑之助拍攝於1903年,泰雅青年半蹲在路邊,不遠處有著漢人服裝者挑擔走來,想是示範獵槍使用方式之作。圖四出自1935年出版臺灣蕃界展望,作者以「他們的最大快樂」為題,可能是布農族的年輕獵人在林間右手持前膛獵槍側身而立,裝著獵物的網袋中有一隻幼豬,說明了獵物背負的方法、使用的獵具及狩獵時的穿著,照片趣味性十足。
獵物非一人所有,要分給共同狩獵的人以及親友,排灣、魯凱二族還要取下一定的部位作為獵租交給頭目。分肉的照片有兩張,都出自臺灣蕃界展望,其一是三名布農族獵人穿了典型的背心在林中處理獵物(圖五)。另一張則是排灣族人在應是頭目階層的家屋前處理獵回的山豬(圖六),四把獵槍依牆而立;兩名成人拿了工作刀處理腳部,另一名則在處理頭部,豬背部朝上,皮已展開,肉及內臟已處理,一旁還有兩隻狗;五名男童圍在兩端觀看,其中兩人裸著上身,一人手上還拿了工作刀,說明了自小便有兩性的區別,和狩獵有關的是男性的事,即使是兒童也不例外。
獵物的下顎骨則用來裝飾家屋,以向人展現屋主的獵績,森丑之助於1905年拍攝的來義(今屏東縣來義鄉來義村)頭目家屋(圖七),屋子正面的屋簷下以獸類下顎骨裝飾,而非一般的木雕為其一;臺灣蕃界展望中的佳平(今屏東縣泰武鄉佳平村)頭目家(圖八),則把山豬的頭骨上、下顎均保留下來,與象徵地位的陶壺放在一起。千千岩助太郎約在1938到1942年之間進行高砂族的建築調查,攝於達拉馬告(今屏東縣霧台鄉大武村)的魯凱族家屋(圖九),動物的下顎骨掛在右牆的上方,以屋子的大小高度及陳設來看,應是頭目的家屋,這兩地獸骨懸掛的位置與近年在聚落所見,懸掛於入門烹飪處不同。
比較珍貴精彩的是鄒的獸骨棚(圖十),干欄式建築排滿獸骨為壁,這是1902年森丑之助在特富野拍攝的。鈴木秀夫的臺灣蕃界展望中,獸骨棚的外貌與獸骨陳列方式(圖十一;圖十二),與森丑之助所攝略有不同,內部密密麻麻全是獸骨,什麼原因導致這種差異,尚待進一步調查。
最後談到豬的飼養,不只是居住在平地的卑南族與南部排灣族(高士,今屏東縣牡丹鄉高士村)飼養豬,居住在較高山區的鄒與布農族也都飼養豬隻,1912年高橋勝雄所編「The
Statistical Summary of Taiwan」一書中的照片顯示鄒族豬與雞共同飼養,豬隻多達五隻,且大豬相當肥大,已無法判斷是野豬還是家豬9圖十三)。臺灣蕃界展望中,台中地區的布農族在前往新的墾地時,除了隨身的細軟之外,最右側的男子抱著一隻大豬,顯見豬隻對族人的重要性,也印證了南島民族攜豬遷徙的紀錄(圖十四)。最珍貴的應屬千千岩助太郎所紀錄的蘭嶼的豬棚結構,顯示雅美族(達悟族)以放養的方式飼養(圖十五);1931年出版、稻葉直通及瀨川孝吉所著「日本?南端 紅頭嶼」一書中,紀錄了雅美族(達悟族)餵食豬隻的情形(圖十六),所攝豬隻符合蘭嶼小耳豬的描述。
臺灣蕃界展望一書中花蓮港廳的種豬場(圖十七),說明紀錄了日本殖民政府對畜牧業的影響,也提醒了我們,這些資料,其實是某個特定時空,紀錄者依其興趣或需要留下來的,看似客觀的影像紀錄有著極主觀的成份,即使是豬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