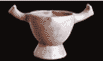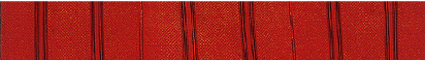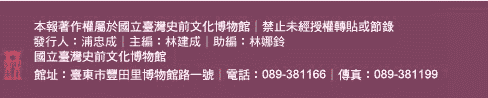史景遷─最會說故事的史學大師(圖摘自《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時報出版) |
一、最會說故事的史學大師--史景遷
2005年底,著名的西方中國史學學者--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的台灣行,引起一陣騷動,就連台灣流行音樂界的搖滾巨星伍佰,都是史景遷的超級粉絲。在簽書會中,當伍佰從史景遷手中接下親筆簽名書時,他興奮地對心中的偶像說,在歷史面前,覺得自己好渺小(註1)。
這位長得很像影星史恩.康納萊的歷史學者,除了少見的帥哥型學者讓人印象深刻外,他的著作也給了我一個巨大的啟發,這個「巨大」的力量,來自於一位西方學者,竟能橫跨東西、跨越語言文化的隔閡,並穿越中國的歷史時空,將中國歷史,以極具感染力的方式轉譯出來,並同時影響了學術界與一般讀者。從此,我也成了史景遷的粉絲。
史景遷的著作被譽為具有「敘事史學」風格,本人則被譽為最會說故事的史學大師,也是一個自覺努力與讀者溝通的轉譯者。文學性,在他的史學著作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如他用他的英國腔緩慢清晰地對「敘事史學」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句話我不太了解。但我喜歡文學,而且我想把過去零碎的歷史片段重新整理、建立,使得過去與現在產生連結。」(註2)
在《追尋現代中國-革命與戰爭》中,他以1921年出版、魯迅的著名小說《故鄉》中悲觀但令人動容的結語--「便成了路」,為包括胡適在內「五四」人物的思維,下了一個極具感染力的註解(註3)。魯迅的全文如下:
希望是本無所謂有,無所謂無的。這正如地上走的路,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史景遷不僅轉譯歷史情緒,更是一個轉譯歷史情境的能手,如他的名作《婦
人王氏之死》的開頭:
1668年7月,傍晚時分,月亮緩緩升起……毫無預警之下市區的建物開始搖晃……樹梢幾乎碰地……。
當多數歷史學者從權力核心詮釋歷史,史景遷則從一位鄉下婦女為主角,以1668年的山東大地震的場景,道出清初的婦女生活與土地制度等。他更具有轉譯歷史心靈的同理心,成名著《康熙》,從先作為人,才作為皇帝的生命意義探索康熙(註4)。
二、術語的封閉與排他性
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行話或術語,高至學術殿堂,小至理髮、「黑手」業界,或特殊族群,如情報工作、同志圈、黑社會。行話有它的明確目的,是給「圈內人」聽的,有時擺明就是故意不讓外人聽懂的「通關密語」。但,行話與術語的「圈內」目的,若擺錯了地方,就常發生了圈子封閉與排他性的問題。
台灣傳統博物館的轉型,就常面臨或不自覺行話與術語目的擺錯地方的尷尬。例如,博物館並非如中研院純學術研究之地,扮演了社會教育的社會責任,但研究人員的學術習慣用語,有時忘記「同理」缺乏基礎背景知識的觀眾,而以已經「進入狀況」的學術程度來呈現(參見同註4)。博物館轉譯的落差以及排他性,常在這種不自覺的狀況中發生,也就常讓觀眾產生博物館封閉與權威的殿堂之感。
博物館其實一直在做轉譯的工作,推廣教育在於「深入淺出」也已成為基本常識。但很少人嚴肅地把轉譯視為一種需要訓練與養成的專業,反而理所當然地視為每一個人都會的基本工作。或許受制於學術升等,或習慣於學術氛圍,而輕忽轉譯,進而忽略投資轉譯的資源比重。這個資源包括專業人才與經費。
轉譯,或許不是種學術、學問,和研究人員升等無直接關係,但卻是最為關鍵的博物館專業,因為它是與觀眾最為密切的接觸點。而不成功、應付了事、機械疲乏的資訊,或不自覺夾雜過多學術行話與抽象語言的轉譯,卻剛好成為觀眾覺得最無趣的折損點。
轉譯,不僅只是將學術行話轉成「白話文」而已,如果博物館自許扮演重要的社會教育影響力,並期望獲得廣泛的迴響,就必須做到具有感染力與深植人心的轉譯功力。
中研院院士許倬雲曾這麼形容史景遷的轉譯功力: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註5)。博物館如此豐富,但若缺乏關鍵的轉譯功力,這些有形無形的豐富,就無法被看見、被欣賞、被深刻感受。
成功的、傑出的轉譯,或甚至能轉譯史前人類、原住民所處的歷史情境與心靈。然而,成功的、傑出的轉譯很不容易,但如何先為達到好的轉譯而用心、而努力,如何區分學術與專業的不同重要性,如何避免接觸點成為折損點,是博物館須先自覺的問題!未來,才有可能如魯迅所說:「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