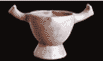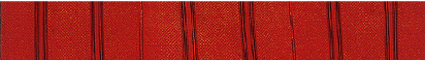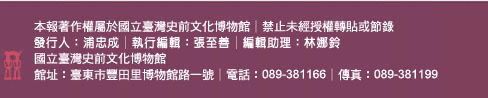家名與繼承
排灣族的家屋通常都有一個家名,這個家名則與家屋成員的名字相聯結,如家谷拉夫.甘比(tjakulavu
kanpi),家谷拉夫是其出生之家的家名,甘比是其名字。家屋在非親屬間產權移轉,家名依舊。同一家人因故遷入另一家屋,則採用該屋原有之名。新建家屋者依例另取家名,但將原家屋主要石材搬運到新址重建者,常沿用其原有的家名。
家庭結構和家戶結成大社區的一個重要關鍵在於社會關係的居處法則(residence
rules)。最重要者就是婚後居處的法則。排灣族的居處法則以種子家庭為核心的新居制。排灣族將原居地稱之為paumaumaq,家屋則稱之為umaq,其是生來之所,也是死後回歸之處。家屋一般由長嗣繼承,留守原家的長嗣稱為vusam,也就是指小米收獲選取最好的一束做為「種粟」之用。vusam亦是留守原家的長嗣與種粟的稱謂相呼應,意在期望小米的豐收與家屋子嗣的繁衍得以相稱。長嗣所居住的原家稱之為qumusam,即「播種」之意,而弟妹創立的新家稱為qusam,即「種子」之意。一個vusam稱他的分家為ku-ngedruq,意指︰分家對於原家而言,如同竹子的一段或繩子的一節。原家必須提供新建立分家耕作的粟種,而分家必須透過回贈原家小米或回原家分食小米。由一個原家分出來的各家,當地人稱為「一個家」(ta-umaq-an)或是「一樣的血」(ta-djamuq-an)或是「一條路」(ta-dja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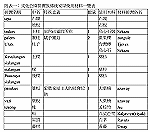
文化公園排灣族傳統家屋使用材料一覽表
|

文化公園傳統家屋室內空間名稱及其意義
|
家屋的空間
家屋執行了久遠的社會功能,最顯著的是那些容納與再現宗教與政治制度、提供遮蔽庇護及支持關係、表現社會區分體現財產關係,並且使地位、認同和權威得以表現。因此,家屋的尺度、形式、功能、區位以及耐久程度等等,都是社會生產出來的。住屋的空間,提供了一個理解家屋和社會脈絡最為有效的出發點。社會需要隨著歷史性的生產方式變化,而不斷的被創造和改變。
如果建築物被社會生產出來,它們也被社會消費,家屋以及它們所在之較大環境,不單只是反映或呈現了特定的秩序,它們還積極的從事社會與文化存在之建構:社會在相當程度上是藉由它所創造的建築物和空間而構成的。
家屋內部空間往往是原住民族宇宙觀之縮影(microcosmos)與再現(representation)。家屋空間取向(orientation)表達成員之間的階序、權力關係,可區辨為舉行儀式的神聖空間(宗柱或祭台)與日常生活的空間(常以爐灶為象徵);家屋中的爐灶常能將聚落外的食物,轉化成為家屋成員共享的食物。
東排灣族的家屋屋頂,有一蓋與主樑相垂直,並且搭接於中柱的一塊椽板,這塊椽板是家屋有祭祀活動時,先對著板子點灑小米酒和祭物之處,祭拜的對象則是adaw(太陽),泛指神靈;而後再走到後側山牆的神龕,稱之為umaqan,意指祖靈的居所,向祖靈告知家裡的事物,並祈求神靈的庇佑。
排灣族家屋之門(paling)有其禁忌,凡是儀式用器物與平地人傳入的物品,都不可穿越家屋之門。這些物品必須由家屋的窗戶進入,窗戶是溝通家屋內外的通道。家屋的前庭才是家屋成員與其他家屋進行日常與儀式性的拜訪(參加婚禮或其他慶祝儀式)的空間。家屋中做為日常生活的空間起居室(tala),也是舉行家庭儀式的地方。因此,平地人的物品禁止進入此一空間。通婚男女雙方的親友之互訪,也多在此處進行。排灣婦女常常坐在家屋內做手工活兒,隔著敞開的窗戶與在家屋簷下(liti-liting)的訪客聊天。
家屋內部的神聖空間,經常以小米穀倉與家屋中柱所舉行的儀式與相關禁忌而突顯其重要意涵。位於家屋內部較後方的中柱是全屋中最重要的柱子。家屋內部空間更常常成為女性子宮的隱喻。排灣族孕婦難產時,必須由家人跑到屋外搖晃家屋來使孕婦順產;若真的發生難產,則必廢棄家屋、另建新屋。女性生產時,家屋內部則完全成為女性的空間,當產婦與嬰兒不幸因難產同時死亡時,其至廢棄家屋,另外覓地重建。
家屋空間之所以可以區辨成為內外的基準,不僅是一種視覺上的實體、客觀的區辨,更需藉由當地人以人與身體的象徵所實際介入的文化實踐過程,來展現出內外區辨的獨特意義。門檻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區辨與實踐的場域,因此,